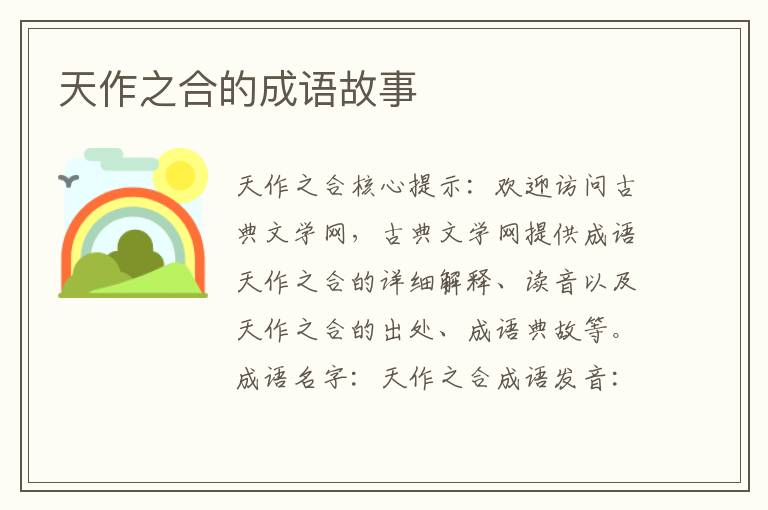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网络整理”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我到现在还过着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报刊的日子。这中间,最彻底的是不上网,我的手压根儿没有碰过电脑,也没见过网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博客,这是九久读书人俱乐部的一位女孩子在工作之余顺便管一下子的。我与她几乎没有联系过,偶尔我的助理金克林会把我的谈话转发给她,但这样的机会极少,只有在5·12地震之后,我谈过几次话。无论是这个女孩还是金克林,都不会把网上有关我的说法转告我。
我不上网,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持方式。因为生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而最有可能夺去我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实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实,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我严格控制自己的信息来源,每天只花极少的时间看一下电视新闻,以国际新闻为主,然后再静心来想一下。
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互联网上一切有关我的谈论,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事实证明,这对我大有好处,使我有时间完整地做完一件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分散精力。但对一些关注我的朋友,可能有点对不起。
我知道,每次网上投票,广大网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好意,这真让我汗颜。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领取“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我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在这里,我把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
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的,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问:您获得“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几本书证明。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慎用“国学”这个概念。这是因为—
一、“国”是一个政治命题,把政治命题压在文化命题上面,很不合适。我历来认为,文化大于政治,自然大于文化。当文化贴上了“国”的标签,很多衡量标准就会产生错位。例如,我曾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残害人性的封建极权主义毒素,但如果说这是“国学的毒素”,就会冲击很多人的爱国热忱。因此,动不动就说“国学”,很可能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
二、“国学”的说法具有太大的排他性。例如,佛教显然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国学”吗?而且,“国”字一套,成了一种唯一选择。说乒乓球是“国球”,那么,排球呢?其他有可能为国争光的球类呢?说京剧是“国剧”,那么,比它更年长、更经典的昆曲呢?同样,国乐、国画、国术、国酒……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曾一再指出,中国文化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创新精神严重衰减,至十七、十八世纪的日益严重。这个倾向,使秦汉唐宋的文化气韵不可复见。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当代创新,就没有传统尊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艺术创造论》中就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观点:传统,不是我们要继承的现成遗产,而是靠我们今天的创新来参与并规定的动态存在。可惜,近二十年来,尽管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中国文化仍然严重缺少创新精神。最近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问: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授牌的时候,网上有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妒嫉。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您能介绍一下工作室现在的工作规划吗?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在中国文化领域,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名词的泥潭里玩水,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必在意。上海市教委早就发觉,目前政府支持理、工科的渠道有千条万条,但支持文科、艺术学科的渠道少而又少,因此在几年前设立了“大师工作室”的规程,这个思路很好。现在,这么大的上海只设立了两个,今后几年有望增加到三四个,可见非常严谨。我们的这个“大师工作室”名副其实地请了一批大师在工作,香港杰出电影导演关锦鹏先生、国际著名音乐家鲍比达先生、形象设计大师张叔平先生,以及另外一批顶尖艺术家都因为这个“大师工作室”而集中到上海,埋头创造了那么长时间,打造了获得一致好评的原创音乐剧《长河》。这件事,已经展示了工作室的几项宗旨:第一,立足于创新;第二,立足于作品;第三,立足于跨界;第四,“大师”是复数。
我会继续召集更多的国际级艺术大师到工作室里来合作创新。
我的工作室的常规工作,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凡是已经在海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如果愿意申请,经过考核批准,可以在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和工作。我现在设定的专业是三个:中国文化史、艺术创造学、城市美学。我已邀请海内外的一些著名学者参与指导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招收的“博士后”人数不会多,现在已有极优秀的专业人士报名。
问:去年网上还议论:您出生的老家申请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