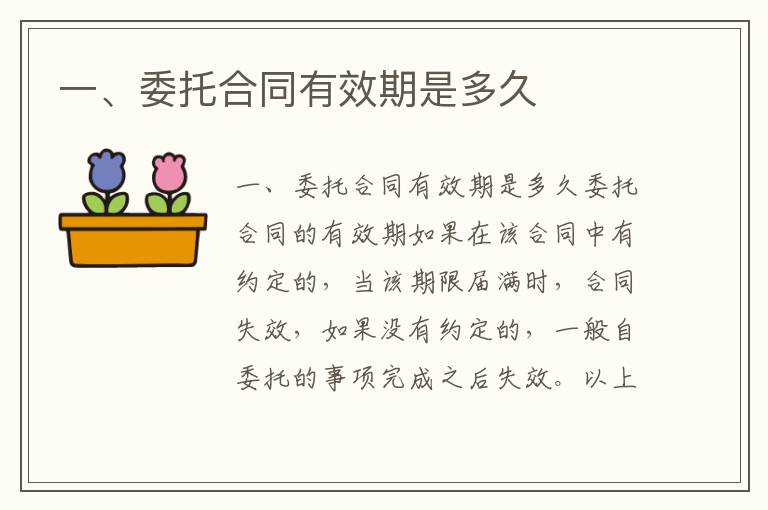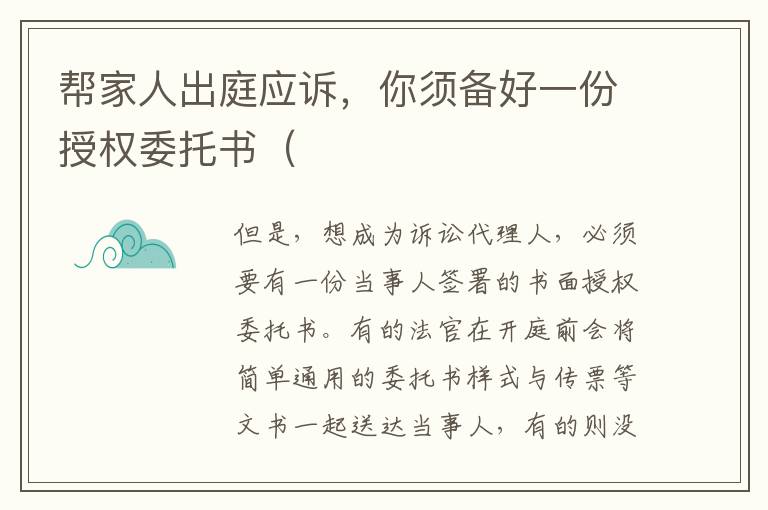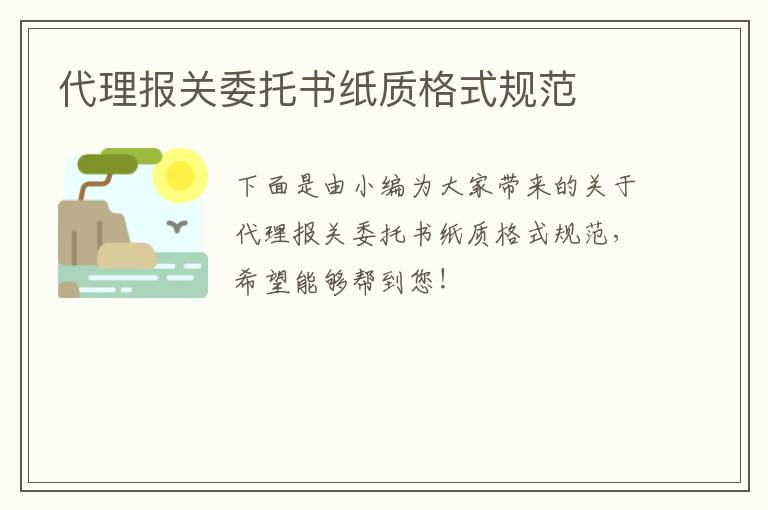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网络”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引言:2016年4月29日7时40分,陈忠实先生因病去世。时光如箭,冬去春来。又是一年白鹿原上桃花红杏花白。陈忠实老汉已走了两个年头。今天,白鹿原上花儿绽放,人声如沸,为了纪念陈忠实逝世两周年,我们特推出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院长黄藤先生曾发表在《延河》杂志的长文《我和》,追思白鹿原上已去的陈忠实老汉。与此同时,《文化艺术报》在2018年4月27日推出的《陈忠实逝世二周年纪念专刊》也专门对黄藤董事长进行了专访,回顾了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的公演之路。斯人已逝,追思为祭。
∆《白鹿原》话剧完整版视频

我和《白鹿原》
作者| 黄 藤
文章原载于《延河》杂志
我不知上天是否真的安排好了世间的一切,但世间的事情冥冥之中好像早已安排定了,我和《白鹿原》便是如此。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我第一次读《白鹿原》是在1993年。那年有两部长篇小说几乎同时出版,另一部是贾平凹的《废都》。那时我正在新加坡一所英文学校学英文,除了上课,没有太多事情,正好仔细品读了这两部巨著。有些情节反复读,以至于一些句子和打油诗都能背下来。我爱人说:“你怎么对这两部小说这么有兴趣?”我说:“我觉得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高峰。”之后,我听说贾平凹被派去张家港体验生活了,《白鹿原》也出了修订版。一切在意料之中。曹雪芹没活到《红楼梦》红遍中国,司马迁也没有看到《史记》被树为国之正传,孔子更是在第二十几代孙之后才被尊重。历史自古如此。比起他们,今天的作家应该是幸运的。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我后来见到陈忠实,并有时间坐下来聊,是因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要让我做一期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因为哈佛大学商学院已经把西安外事学院确定为他们商学院的教学案例,这是至今哈佛大学商学院唯一一个中国高校案例。这期节目陈忠实先生来了。之后,曹景行先生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也来了,并送给了曹景行先生一本自己签名的《白鹿原》。我陪他向餐厅走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半开玩笑的说:“陈老师,你怎么知道人家白嘉轩在洞房里干了什么?鹿子霖怎么算计白家?你从哪里查的资料?”这时,他看着我反问了一句:“你说这么些年人性变过没有?”我猛然间如醍醐灌顶,用手掌根儿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然后竖起大拇指对他说,“高!”心里说,是啊!几千年过去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变过吗?没有,科技进步了,物质条件变化了,但人性没变。一部作品,根本就是作家思想的展现。作家有多大的心胸,作品就有多大的画卷;作家有多高的境界,作品就有多高的立意。一切根本不需要知道任何具体的细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在作者胸中。所有画点都是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对人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没有更多的语言,一路只是走着,但我已感觉到两个人心里已然相通了,心照不宣。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这可能使得我后来和陈老师见面和沟通更为顺畅。陈老师爽快地给我写字、送书,什么时候打电话、写短信都耐心回应。他爱足球,《三秦都市报》举办足球联赛,就用我们学校的操场,请陈老师和我一起开球,我把球踢给他,他把球踢出去给运动员,比赛就开始了。他高兴的笑着,脸上的皱纹依次绽开,像孩子一样可爱。
我从小理科学得很好,数理化很少有九十五分以下的成绩,一直到读完高中。在工厂、农村搞过很多创新。但命运就是像安排好的一样,我进了大学的中文专业。一开始痛苦不堪,从古至今,典籍文章,经史巨著,浩如烟海,倾其一生恐无法尽览,但越读越是喜欢了。我强迫我在纽约大学读大一的儿子,一定要考北师大的中文专业,用现代化带来的便利读网络大学、在纽约读中国大学的中文专业,不能脑子里只装着那些洋码字,要把方块字和它承载的五千年文化融进血液里。就像白孝文说他是白嘉轩的儿子,白家的家训已融入了血脉一样,炎黄子孙就得把儒家文化融入血脉之中,这在冥冥之中也注定了我和《白鹿原》的不解之缘。
西安外事学院从1992年起,就一直试图探索在某一个领域能够成为自己和其他公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平台,我们一直在影视方面进行探索。刚好我的儿子在五岁的时候,被香港导演马楚成带去拍了《浪漫樱花》,当时和郭富城、张柏芝一起合作。从此,我也认识很多影视界的导演和演员。北京人艺在陕西演出话剧《白鹿原》的时候,直接点名了外事学院的学生做他们的群众演员,所以我们也全程跟踪了北京人艺话剧版《白鹿原》的陕西演出。
接到排《白鹿原》话剧的任务是陕西省文化厅刘宽忍厅长打来的电话。他说娄省长(现在已是陕西省委书记了)对《白鹿原》很重视,要求排一个话剧,因我们有基础,希望能尽早在高校巡演,文化厅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当时我并没有兴奋,但觉得是一个契机。现在想来,最幸运的是排演了《白鹿原》。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由于自己和文学、和陈老师的缘故,《白鹿原》的全部改编我都极其关注。北京人艺排演的《白鹿原》话剧,我看过两遍。由于小说部头大,人物线索多,他们用了三个半小时。导演又想突出陕西特色,用了陕西话,加了华阴老腔。陕西味儿很浓,但总觉没有过瘾。后来我期待已久的电影《白鹿原》终于上映了。我怀着兴奋和崇敬的心情地带着全家去看。电影没演完我就走了出来,这在我看电影经历中,至今只有这一次。心里实在难受得不能坚持。也看过自己觉得比这更差的影片,但可能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心情也就没那么沉重,有时候笑笑就过去了。但《白鹿原》我实在笑不出来,只觉得憋得慌。现在自己要排话剧《白鹿原》,还是省长、省文化厅官方正式的安排,一种沉重的压力和责任迎面而来。但我已下决心皆尽所能,一定搞好。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我拨通了陈老师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并希望当面与他商量此事,听他的意见。他说他在医院,情况不好,一切由我自己看着办。我召集了我们影视艺术学院的全部主要力量,包括兼职的教师共同商议,大家一致意见是排一部能与一流院团水准相媲美的话剧,并认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政府的支持给了我们机会,就一定要做好。
说时容易做时难,整个排演过程并不顺利。因为要一流,我们从编剧下手,先请原来人艺的编剧孟冰先生,我和他见了面,结果被非常谦和地婉拒了。又请我省的大编剧芦苇先生谈了两次,种种原因未成。一切求人的努力都失望之后,只有自己干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团队,是一个混合体,专业的、非专业的,署名的、不署名的,今天他来了,明天他可能又走了。编剧、主演、导演们累了都有情绪,争吵、撂挑子。晚上躺下来睡不着觉,想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我写了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这半生,
我用黄藤搭了根独木桥。
二十几年,
已有几十万人走过。
彼岸,和阳关道是同一个。
没有抱怨,也不嫌它窄小。
揪心的是,
那么多人,竟挤不上这草藤桥!
现在,藤更黄了,就要枯了。
还有几片青叶
就用它的青色画吧。
画一座脚不能踏,
心却能过的桥。
再也不用攀爬,拥挤,
所有的灵魂都能过去向往的美好。
笔在手上时才感到如此沉重,
一点儿也不比搭桥轻松。
我怀疑我还有没有力气,
更怕画不出好的景致。
一个声音,从心底传出,
“藤黄了,叶还轻;
发白了,心还红。
画出的桥
永远不会变黄,干枯。
为她,你值得挤干最后一滴绿汁。”
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为什么会成功,如果有人卖给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了。我不知道陈老师是否也是如此,必须自己滴出心中的血。种种的磨难都已过去,苍天不负人,2016年1月6日,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如期在西安索菲特剧院登台试演了。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为了客观评价演出的效果,找出需改进的问题,我们和文化厅一起,在北京请了十位专家,省内也请了几位评论家,有欧阳逸水、刘彦君、黎继德、汪守德、顾夏阳、赵红帆、胡薇、朱佩君、肖云儒、李星、孙豹隐、莫伸、李国平、仵埂等,大家给予了一致好评,李星先生说:“话剧《白鹿原》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改编演出,更是主创人员及西安外事学院向陈忠实及原著的一次庄严的致敬。”孙豹隐说:“这是一台大戏,一台独具特色、气度不凡的大戏。剧本在择取原著焦点与多景式展示原著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比较适当的表现,田小娥被杀之戏,处理的比其它同名作品要好。”艺术家们也对音乐、演员、舞美提出了很多意见,希望改进。
我亲自打电话请陈忠实老师来看,他仍说身体不好,可让家人看看,我们便邀请了陈老师的大女儿陈黎力。她来时带了约40个家人和亲友,我们措手不及,原先只在前排留了几个位子,只好见缝插针,把他们安排在了不同的座位,有的座位已非常靠后或偏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个遗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看完后即表示这是比较好的一部戏。也许是她们向陈老师汇报了情况,我不得而知,陈老师打电话给我,问有没有录像。我说全部都录了,而且请了北京的专业录像,带子还没出来,但我们学校自己录的出来了,效果可能略差。他说没关系,送他看看,并问我是否能在全国公演。我说我也很希望能公演,这需要他授权,最好是书面的。他说明天上午10点,你来我石油学院的家。在这之前,他只通电话,我只要说去医院看他,或请他当面给剧本提指导意见,他都态度很坚决的拒绝了,这是一个破例。我怕他写字困难,马上让律师写了个委托书,只留下空白的地方让他签字。第二天我和我们学校的宣传部长王文,还带了个摄影师一同去陈老师家里,提前买了些鲜花和营养品、水果。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2016年1月12号上午9:30分,我到石油学院他的家属楼时,王文已先到了。王文说已和他儿子联系过了,儿子不在这边住,如果大门开不开,他爸会把钥匙从楼上扔下来,你们开门上去就行了。幸运的是大门开着,我们直接上了三楼。敲了几声门后,陈老开了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他的一瞬间,我完全呆了!我从没见过陈老师这种表情和脸色,皱纹依旧,但全不见了在足球场上的那种上扬,一脸土青色,只有几缕灰白色的头发还朝上背着。我心里如压了一块石头,沉重的不能喘气。我直觉到这可能是最后的见面了,不幸的是,让我言中了,这真成了我和陈老师最后一次见面。
他看了看我带的打印好的委托书,坚定地说:“不用这个,我给你写。你们稍等一下。”说完他就回里屋了。我没跟去,在他回屋后,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座位两旁堆得比他坐下还高的书,一幅速写的素描像放在最高处。上面已是一层土了,连茶几和扶手上,都是灰,显然连擦拭灰尘的心情都不再有了。我突然想到了耶稣,想到了释迦摩尼,多么希望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什么神都行,至少能让人坦然面对谁都逃不开的结局。但这个结局不是悲伤和无望,是希望、新生、美好,是自己一生最理想归宿。正在乱想,陈老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刚写好的委托书交给了我。我接过一看,上面清晰有力的写着:“著作权许可书。许可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先生将拙著《白鹿原》改编为话剧本并实现舞台演出,免收剧本改编费。仅此说明。”最后是他的名字,并盖了篆刻的鲜红印章。我主动紧紧握住陈老师的手,感觉一股压力,同时也有股力量传递了过来,认真而坚定地说了一句:“我一定把他搞好!”临走的时候,陈老师看着一篮水果和一兜营养品说:“都拿走吧,吃不了,过两天都坏了。”而且非常坚持。我只好同意让人把除了鲜花以外的所有东西拿回去。这时随我一起来的摄影师从包里掏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白鹿原》,请陈老师给他签名,陈老师欣然拿了书,又回里间了。借这个空档,和我一起去的王文,把东西放在茶几后面不显眼的地方。陈老师出来,摄影师接了书、道了谢,我们就走了。下到二楼,陈老师又喊住我们:“让你们拿走就拿走,别留这些东西,吃不了。”我只好又返回去拿了东西,但还是趁他不注意把一盒不大的即食燕窝留下了,希望他哪怕能吃一口,也是我们的慰籍。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之后的几天,我没有太多话,满脑子是见到他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景象,我到的分明是他的书房,可是却蒙上了一层天堂的影子。我的心情沉重、压抑。之后,面对悼念他的铺天盖地的花圈和摆满鲜花的灵堂时,那书房的一幕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似乎在那一握手之间,他把心中积压的那些说不清也没法说的东西都传递给了我。
自由激发了我所有的活力,受托感到一种责任和压力。我立即到了我做过访问学者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是我的导师。我顺利地订好了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进行话剧《白鹿原》的演出,又托人想在其他高规格的剧院能演出。很幸运,保利剧院有一家一年前就订好的演出时段,由于部队整改不演了,把时间让给了我们。吴京安导演也凭着他的人脉定好了天津、山西、南京的演出。我立即将这些消息借着过年拜年,用短信发给了陈忠实老师。能让陈老师在离世之前,得知《白鹿原》能公演,这是至今让我最为欣慰的事。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要把陈老师的作品搬上北京的舞台,对我们是极大的挑战。因为北京舞台上已经上演过同名的话剧。但我们是陈老师亲自主动委托的一次演出,只有尽我之全力,方能安心。因此,我又召集全部主创团队,从剧本、音乐、舞美进行了很多调整,音乐干脆是重新制作,演员也调换了6个。这次全国巡演,省文化厅也全力支持,免费提供了人民剧院的舞台,还因此调整了其他院团的演出,把4月30到5月8日让给我们《白鹿原》剧组。4月30日至5月3日合成,5月4日彩排,5月5日至8日正式演出。我们以校园戏剧的角色出现,也因此得到了教育工委、教育厅地大力支持,发文让各学校来看。我们也请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我所在的党派——民主促进会的成员来看演出,各方都很支持。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我希望陈老师能看到再次修改后的版本,并精心安排录像,计划再送给他审看。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这时,陕西诗歌网组织了著名诗人进韩城活动。韩城和黄河、司马迁相关,勾起了我的思绪。《白鹿原》似乎是黄河厚重泥土的堆积和承载。陈忠实似乎和司马迁一样,用笔描绘着历史的画卷,有着一颗孤独的内心。于是我推掉了一个签约仪式,让人代替了;学校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没有参加,让校长代我在开幕式上讲话。我和一群诗人相伴,依然前往韩城。我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从黄河岸边归来,要去司马陵拜谒的早晨,手机传来了一条短信,说陈忠实先生去世了。一开始怀疑其真假,很快就被证实了,很多人都收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憋在胸口,该写点什么了,这是第一反应。心又特别慌,不知道写什么。 站在司马迁陵上,我觉得文人、作家、史学家、有责任的人、那些头脑过人的人,是不是都必经经历苦难?不用到现场我就能想象陈忠实老师葬礼的隆重,就像我脚下司马迁陵的雄伟。可为什么要他受那么多磨难?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都必经如此吗?另一些词由然而出:
我知道,你不在这儿。
是的,很多年了,
空坟头上,
已是大树参天!
我不知道,
你去了哪里,
是否依然悲愤?
尽管,功成名就,
题碑一片。
我听到了,
从水底传来你呐喊的声音:
“我深爱着的国,
我深爱着的家,
我深爱着的人,
虎门欲束声,
更是涛如吼!”
我知道,人的肉体会死。
你干脆让那被残缺的躯壳,
像基督的圣体一样,
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灵魂,
也有天堂?
尽管,所有的磨难都已铸成千古绝唱。
我看见了,
你就在那儿,
无增无减,本性永恒!
我深爱着的国,
我深爱着的家,
我深爱着的人,
黄河最窄处,
景色成绝佳。
我的脚站在司马迁的陵上,内心却在悼念陈忠实老师。尽管这样的结果,早有预感,但还是觉得太过突然。我立刻打电话,让办公室赶去,以学校、我个人和剧组名义各送一个花圈。下午,车回到作协时,我在门口看到了这几个花圈。正式的吊唁第二天才开始,灵堂是空的。我自己一个人深鞠了三个躬。又和回来的诗人们自发一起再拜了陈老师。我当即决定把4号晚上的彩排改成追思演出,联合了陈老师生前任客座教授的几个大学,组织了一个自发的追思会,并请阎安副主席协调作协能来一起参加,后回话由于第二天有告别仪式,太忙。我又请他协调让剧组参加告别仪式,他鼎力相助,让我们几个主要成员看到了陈老师最后的遗容。
追思会的当晚,九所大学的校领导和师生、教育厅领导都来了,座无虚席。晚到的只好坐在过道里。没想到的是副省长也来,并表示这只是个人身份,不要宣布和介绍。肖云儒先生和文艺界的朋友也来了,新闻单位有十几家要求一同主办,会场严肃而井然。尽管是排演,演员非常认真,最后专门加设了向陈忠实老师遗像集体鞠躬的仪式。这个仪式一直保留到之后的所有演出。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期间,娄书记秘书来电话,说书记指示要买票观看,但他买不到票了,让我们设法卖几张票给他。而且坚持说一定要买,我说一定卖给他。之后省委宣传部陈彦副部长带着省内几位专家也来审看了演出。六位副省级以上领导、十几位专家,前后8场,一万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接着,剧组就要奔赴北京演出了,娄书记的秘书又来电,说书记指示要请陕西在京的领导观看演出,请你们做好对接。我义不容辞,匆匆赶向机场飞往北京……
(全文完)
《文化艺术报》在2018年4月27日推出的《陈忠实逝世二周年纪念专刊》也专门对黄藤董事长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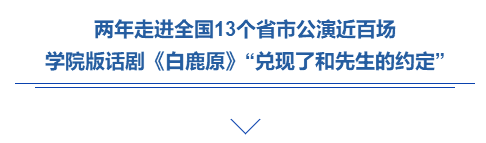
如果说,两年前西安人民剧院的那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两年后,当学院版话剧《白鹿原》走进了北大,走进了北京保利剧院,在全国13个省市巡演,公演场次近百场,收获好评如潮时,作为该剧出品人的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心终于定了。“这样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它已经能称得上是一部‘向陈忠实先生致敬’的好作品。”
斯人已逝,“白鹿”犹在。在陈忠实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这部刚结束全国巡演的校园版话剧《白鹿原》兑现了它与陈忠实先生的一个约定:在全国公演。
公演曾获陈忠实亲笔授权
文化艺术报:请您谈谈外事版话剧《白鹿原》是在怎样的初衷下诞生的?
黄藤:外事版话剧《白鹿原》的诞生,其实是多条件、多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是核心推动力还是省领导和省文化厅的重视与支持。
1993年,《白鹿原》小说第一次出版时我就读了,后来我和陈忠实先生一直有深厚的私人交情,并与他多次进行过文学方面的探讨。我自己与《白鹿原》和陈忠实先生的种种渊源算是这部话剧《白鹿原》诞生的第一个基础。
2013年北京人艺排演的话剧《白鹿原》来西安演出,我们学校的影视艺术学院院长赵思源带领表演专业的23名学生全面参与了演出,这是另外一个诞生的基础。我们学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演代教”,《白鹿原》就是我们重点教学的范例,在学校就有广泛的演出基础。
后来因为省领导很重视,文化厅给了经费上的支持,我们就开始了学院版话剧《白鹿原》的排演。
我们接到任务时,希望能够把它制作成一部能够真正领会小说《白鹿原》,真正表现《白鹿原》精神风貌和精神实质的话剧,我们就自己组织班子,自己改编剧本,自己来排演。
我们当时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外事学院不是一个专业的剧团、文艺团体。省领导和文化厅又非常重视,担心学校拍出来的是业余水平,不能承载和代表陕西形象。这时,陕西人艺就承担起正规剧团排演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的任务,实际陕西人艺的彩排和动手在我们之后。
那么陕西就出现了两台话剧《白鹿原》,我们这个版本是重新改编,写本排演的。两台话剧《白鹿原》同时在陕西的舞台上演,而且都走向了全国,两家都获得了好评。
陕西省委宣传部给了我们特别的奖励,将我们排演的话剧《白鹿原》定位成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而且给了很高的现金奖励,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文化艺术报:这一版的话剧《白鹿原》与陈忠实先生之间有什么故事呢?
黄藤:接到任务后我和陈忠实先生联系话剧排演事宜。陈老师告诉我,他身体不太好,但全力支持我们的排演。2016年1月6日,这部话剧在索菲特大剧院试演时,陈忠实先生的家人观看了演出,后来剧组还把话剧录像的光盘送给他看,他非常满意,并问我是否能在全国公演。我说我也很希望能公演,这需要他授权,最好是书面的。他让我去他石油学院的家。在这之前,通电话时我只要说去医院看他,或请他当面给剧本提指导意见,他都态度很坚决地拒绝了,而这次是一个破例。
2016年1月12日,我在陈忠实先生家中拿到了他写给我的著作权许可书。上面写道:“许可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先生将拙著《白鹿原》改编为话剧本并实现舞台演出,免收剧本改编费。谨此说明。”最后是他的名字,并盖了篆刻的鲜红印章。我紧握住陈忠实先生的手,感觉一股压力,同时也有股力量传递了过来。我对他坚定地说了一句:“我一定把它搞好!”
开创“艺术出校园”新模式
文化艺术报:您曾说过要以“一部别具特色”的校园版话剧《白鹿原》向陈忠实先生致敬。如何理解这个“别具特色”?如今看来,它达到您心中期盼的目标了吗?
黄藤:所谓区别就是要和它已有的改编版本有所区别;所谓有特色,就是把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的精神实质和内核表现出来。陈忠实先生对很多改编是不满意的,见完先生后,我感觉责任和嘱托就更重了。我在后期对这个剧本又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使之更加完善,我将这些消息都告诉了先生,但是他还是没有等到我们的全国公演。去世的时候刚好我们在演出,所以我们专门做了专场悼念演出。让我欣慰的是,先生知道并且看到了他的著作从头到尾的改编,从交谈中感觉他很满意。
这部戏上演两年,完全达到了我的期望,第一,演出场次远远超出我们的预计,我们本以为这部剧在陕西本地公演,基本上做一个教育系统内部的巡回演出,这是当时排演时的计划。但是如今我们走向了北京,走进了北大,走进了保利,去了福建、去了上海、去了很多地方。而且都在大剧院,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现在的场次都接近百场了。这样的演出数量与规模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另外,我自己主演的白嘉轩版制成了视频版,在陕西台播出,这就使得《白鹿原》的受众群体成倍扩大,这是其他任何一部话剧都不具备的。包括政府的立项奖励等都是远远超过我们预计的。

∆西安外事学院版《白鹿原》话剧剧照
文化艺术报:两年来,学院版《白鹿原》收获了众多掌声。您认为它的诞生,对学校、对社会来说,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黄藤:过去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总是倡导精品艺术文化进校园,好像校园就是需要被文艺界或者艺术工作者普及的阵地。众多实践证明,大学才是诞生真正艺术的地方,真正的艺术、精品的艺术、有思想性的艺术应该从这里走向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艺术走进大学。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研讨,互相提升的状态。也就是说,学院版话剧《白鹿原》是我们创造的精品艺术出校园进社会的一个新模式。 (来源:文化艺术报记者 梁飞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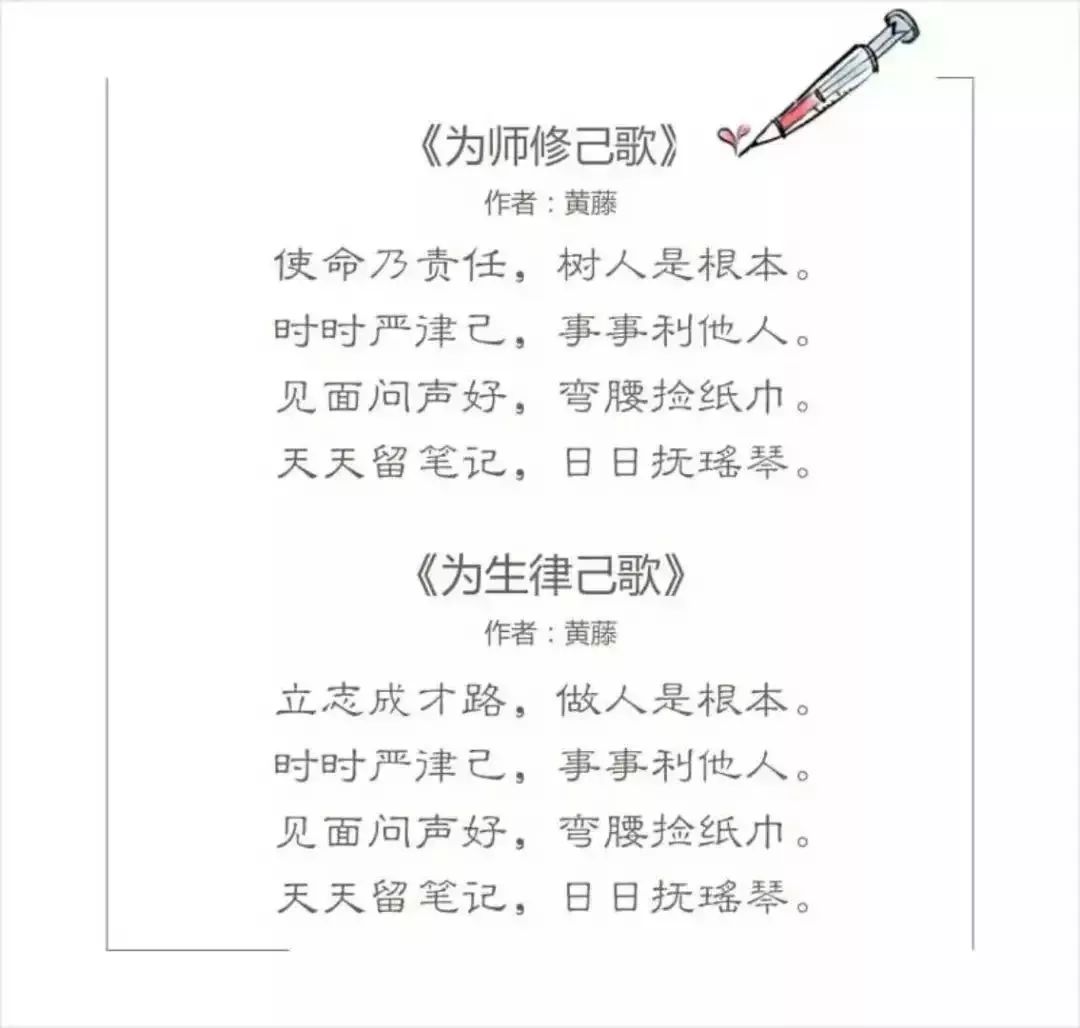
校对 | 朱泽坤 蓝虹 李欣旸
编辑 | 张郁璐
审核 | 李 浩